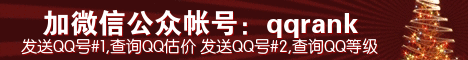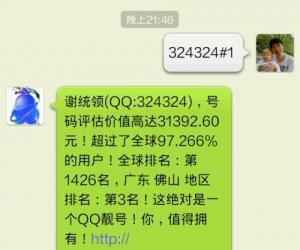陈平原做客腾讯书院:谈“文学”如何“教育”
发布: 2013-4-16 13:05 | 作者: 小谢 | 查看: 1957次

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做客腾讯书院,谈“文学”如何教育
文学该不该进课堂?创作能否被讲授?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?在这个大学愈发功利的年代,人们反复追问中国的文学教育该何去何从。4月12日晚19:00,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做客腾讯书院,谈“文学”如何“教育”。
李白杜甫毕业于何处?
陈平原一开始便提出,文学是一个门坎低、但堂奥极深的“专业”。上大学不一定就能学好,反过来,不上大学也不一定就学不好。
在古代,文学并不是一门正规的学科。
“试问李白、杜甫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?”
同时他也提到小学毕业的沈从文自学成才,从1923年曾在北大旁听,但那无关紧要;结识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林徽因等作家,或许那才是关键。“也有正儿八经留学 (微博) 的,可所学专业跟其日后的文学创作距离十万八千里,鲁迅曾在仙台读医,后来弃医从文,还有九州大学的郭沫若,因耳疾无法从事医学。”
晚清以后,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“词章之学”,转为知识积累的“文学史”。也就是,学唐诗并不一定要写唐诗,学元曲也并非为了作元曲。这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,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换句话说,大学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,是培养兴趣、提高修养,而不是造成多少“作家”。

“文学”如何成为“教育”
对于“文学”的定义,陈平原引用了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的界定: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作品的总称。其后的问答环节中,陈平原也叙述了自己心目中的文学,“用精致的语言,准确地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感受。”
但古代对“文学”作为“专业”的概念很偏颇笼统,与如今相距甚远。
直到1901年蔡元培的《论堂教科论》对知识进行分科,其中的“文学”初具现代文学学科模型。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大学堂,并“参考列邦”把外国学堂copy到中国来,将“辞章”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。第二年张之洞上呈的《学务纲要》强调学西方不可忘本,“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”。“文学”作为一个科目才真正建立了。
三、历史名师片段探讨理想文学教育
康有为在文学学科化之前的讲课,被陈平原称为“今天有哪个教授这样讲,非被学生哄下来不可,随便一句话都是博士论文。”更适合“坐而论道”。
而鲁迅在北大讲小说史常引发教室里阵阵笑声,因为他不仅讲小说史,还穿插“小说作法”与“文化批判”,并“随时加入一些意味深长的幽默的讽刺话”。
朱自清在清华曾尝试将“新文学”学院化,开设了“中国新文学研究”与“中国歌谣”。然而由于当时浓厚的尊古气氛而未能取得较大反响。
中央大学的教授则过着“文酒“登临赋诗”的雅致生活,教育上也更提倡对摹拟更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,完全不同于注重学术研讨的北大。
西南联大的沈从文,虽没有教学系统,但他对学生非常用心,常在作业后写长长的读后感,有事甚至比作业本身还长。陈平原说,如果创作可以教,就应该像沈从文这样“因材施教”。“问题是有这样的人吗,有这样的机会嘛?”
仅存在于“追忆”中的教师们
“文字寿于金石,声音随风飘逝。”陈平原感慨,“当初五彩缤纷的‘课堂’,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。”
他提到被时光遗忘的教学大师——顾随。这是一个会讲课而不会写论文,鲜少出作品的老师。若没有其学生叶嘉莹的奔走呼吁,他可能已淹没于历史的尘土里。
如今我们谈起大学教授,往往只提他留下的著作,而他的本职——精彩的授课。因为课堂转身即使,无法像文字得以保存流传。其实这是偏颇的。
陈平原说:可大学教授的本职应是“传道授业解惑”。
而对于学生来说,直接面对、且日后追怀不已的,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“章程”或“课程表”,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。
优秀的讲师是只存在于“追忆”中的。
完全非功利的文学教育太绝对
如今大学生的学习与阅读越来越功利,陈平原虽然呼吁大家热爱阅读热爱文学,也承认文学是脱离生活的一种精神享受,对于不是中文系的学生来说,文学是“没有用的”。
在问答环节中,一位提问者指出,只有在完全非功利的教育下才能培养出文化大师,而如今的教育体系只有文字行使,而缺乏文化内涵。
陈平原说,非功利性的教育、完全地排除功利的阅读,“这样说太绝对了”。“过分强调你所有的东西是非功利的,我觉得有点不负责任。”如今的学生在整个的学术过程中有功利的一面,也有非功利的一面。“我只敢说在功利的阅读、思考、写作的时候有一种超越性。”